人是有记忆的,所以在适宜的人生经历和时间长度的积累后,在某个恰当的时候,可以怀旧——怀念旧时的一段时光。最经典的恐怕是张氏风格:寻出家传的霉绿斑驳的铜香炉,点上一炉沉香屑,沏上一壶茉莉香片,等香灭了,茶淡了,故事也就讲完了。个人的旧日时光再次闪烁光亮,随即覆灭,那也不过是一炷香、一盏茶、一根烟的工夫。
孩子出生的时候,是她把新生儿从医生的手里接过来抱到产房的。孩子的姥姥说,让姑姑抱,谁抱的将来就像谁,不仅相貌,还有命运。大概老人觉得她还是个顺利吉祥的人。她是小孩唯一的姑姑,把赤条条的新生身体接过来,也不算分外的事。婴儿的身体轻软,刚刚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,像一片粉红的荷花瓣,开在纯棉布缝制的襁褓里。是当年秋天新熟的棉花,新买的花布,一个小人儿被裹在同样轻软的棉里,连带着抱她的人都柔软了。
花落而果实成就后,太多的是坚硬。对物,对事,对人,对这世间。壳,就是这样炼成的。
10月底的天气,医院的楼道里有微凉的秋风吹进,她努力弓着身子,想给新生儿以最安全的保护。从单纯的水世界来到这嘈杂而福祸不定的陆地,显然她还不太适应。
年轻的夫妇让她给新生的孩子起个名字,最后逃不过这个重任,就轻声说了一句,就叫“赤”吧。单一而纯净,她是这样给他们解释的。就叫“赤”吧,看似随口随意,她却相信自己预谋了很久。预谋了很久,没有人知道是因了一个纪念。没有人知道。她若不说,这世界上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,第二个人是仁慈的上帝。
到底还是想留点痕迹。她想。到底,不曾离去。
她认识他的时候,正读大学,人生中顶级灿烂的一段时光。青春时代的恋爱程序大致如此:相遇——躁动——相爱——分手。相恋不是没有结果,只是,分手是结果中最多的答案。那也不白爱,花若不在春天开放,热烈如火,呈赤色,青春就不算热烈。青春不热烈,人生就留有遗憾。日后若有兴致怀起旧来,却没有旧可怀,岂不令人扼腕叹息。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。这人生,就逐渐丰满繁盛起来。
单一而纯净的,恐怕不是春花,而是那段相遇。他说,女儿12月出生,正赶上下大雪,暮雪纷纷,无声地在所有裸露的地方堆积,变得厚重。他视女儿如珍珠。
她亦视与他的相识为珍珠,视那段顶级灿烂的岁月为珍珠。深海是如此的遥远,陆地上的人们看惯了草木,不易得到珍珠。听说珍珠要深海里的最好。20世纪初“泰坦尼克号”豪华游轮上,女人Rose拥有价值连城的项链“海洋之心”——却是钻石做的。她的珍珠和Rose的钻石有一样的结局,都归入海里,只不过Rose是真的把“海洋之心”扔进了大西洋,而她的放在心中,是永远不可测量的深海域。女人的往事,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朝代,不分贵贱贫富,都有一样的开始或一样的结局。收藏起来的就是往事,隔年也许会像旧上海的妯娌们,把娘家的陪嫁拿在太阳底下晾晒。上好的皮子,杭州的丝绸罗缎,轻飘飘,陈列在阳光下,扬散着腐气——旧式女子的樟木箱笼里埋藏着腐气,她的往事里没有,颜色依旧鲜亮,有一份轻飘和光滑的隔离。
走在前往中年的路上,看着不远处董桥开的“下午茶”茶馆,她想,如果每个女子的一生都注定不会只与一个男人有故事,那最好故事就是如此的简单和疏离。曾经在彼此寂寞的青春里说了很多的话,日后又不需要相互承担,也浓烈,也淡远,好像幻觉。而把幻觉进行到底,只是为了青春不寂寞。
他们后来很少见面。说起来也很奇怪,说分手,分后以后就真的没再牵手。哪怕目光,都不曾两点一线地相连。青春恋爱如此决绝,如此不拖泥带水,不暧昧丛生,可真是简单而干净。
只有一回,若干年后,他们在5月里相遇。他摇下车窗喊她的名字。城市很大,人群拥挤,如果不相约,邂逅的概率很低。人和人之间,其实是想陌生就会陌生、想熟悉就会熟悉的,事在人为。可有些人,即使隔了数年的光阴,早不复是当年的红花郎、紫云英,也会在目光相碰间认出彼此,以及旧时春光。
车驶过一条小巷,沿路两边生长着茂密的蔷薇,足有几百米深,开满了蔷薇花。风一吹,红色的重叠繁华就落了一地。这曾经是他们喜欢的颜色和花朵,还有场景,以及略带伤感的情绪。能说什么呢?寒暄和提问都会显得生疏,他们都想记忆曾有的亲密。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,在成长的单薄和寂寞之际,他们曾经交颈取暖,互相安慰。他还是笑着提及了一下往事,最早在你们学校附近的紫光电影院,通宵的电影,你睡着了,我竟不敢吻你,就像我现在亦不敢触摸这红色蔷薇花。她说,我有一次去海边,意外地发现海边有几条蔷薇花植成的花架,红色的、粉色的、白色的,花朵繁盛而重叠。从花架下走过,不远处就是沙滩和渤海,回头一看,我还是喜欢红色蔷薇。
车开得缓到不能再缓,已经近乎停止。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,干干净净,虽如梦幻,却犹在眼前;虽在眼前,也只能当做幻觉。
他们看到有红色蔷薇花瓣纷纷坠落。路的尽头,她下了车。南辕北辙,他们必须各走各的路了。有的分别实在是不需要说再见的。回味是一种温暖,实践却会带来慌乱。此时不是彼时,彼时决绝,此时是分外清醒。所以无须指责。他在分手时说,我有孩子了,女孩,冬天生的,叫“赤”。
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,他们曾指着蔷薇架说,蔷薇花的花语是爱情和思念,红蔷薇的花语是热恋,你要记得。情正浓时,他们商量,将来生女孩,就叫“赤”,恰如蔷薇红。这是花前月下的誓言。
只是,“不向东山久,蔷薇几度花”。花老,山老,人亦老。
回娘家的时候,赤颠颠地跑过来,伸开胳膊要姑姑抱。她伏低身体,把头埋在赤小小的胸怀里,听她口齿不清地叫姑姑。她已婚,因习惯性流产,不育。如今,赤已7岁。那日,她到底没有告诉他,她有一个侄女,名字也叫“赤”,是为了忘却才留的纪念。就让一个孩子做一辈子的提醒吧。这是个秘密。
怀的是旧,颜色却不斑驳疏离,是一截鲜亮的赤色光阴。黑白色的梦境里,恍恍惚惚,偏就顶属青春的那段时光,鲜艳如初,如新日,如红枝蔷薇。
香灭了,茶淡了,故事也就讲完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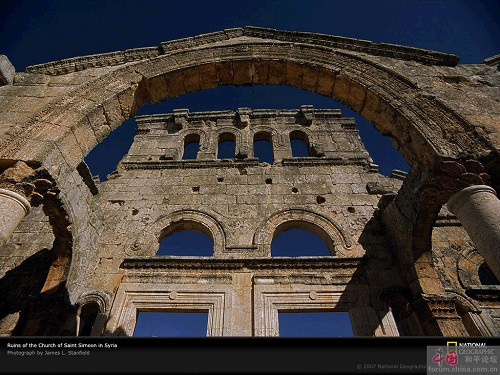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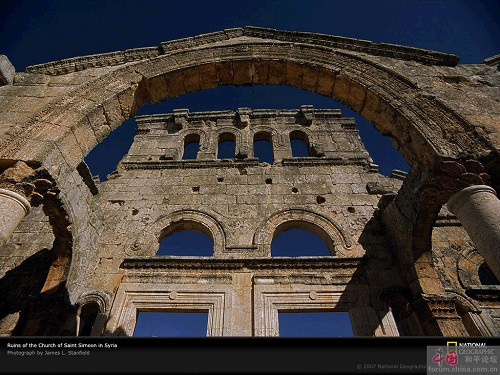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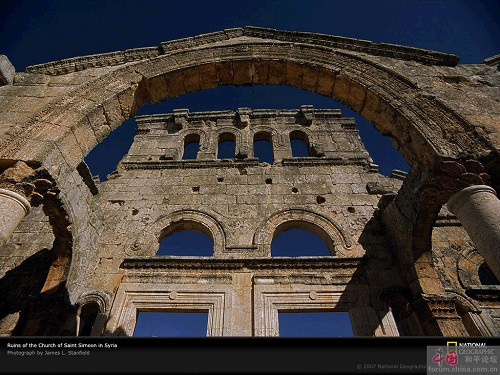
 收藏
收藏
评论
登录后你可以发表评论,请先登录。登录>>